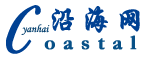吾乡吾民:归家记者眼中的家乡之变
随着集镇化的加速,很多村民搬迁到了集市。于是,养猪的人少了。
关于杀猪的记忆开始在谢子能这一辈消失。
谢耿峰小时候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猪。经常很早就被杀猪声吵醒。那时候,村民们养的猪,都是自己屠宰后拉到集市上去卖。后来屠宰和销售猪肉这事就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了,得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监管。
于是很多人觉得肉价自己定不了,索性不养猪了。村里外出打工的有增无减,剩下的老人和小孩为主,而养猪是个体力活,老人们于是也不养猪了。再加上精壮劳力外出打工,种粮人少了,可喂猪的粮食也少了,这又流失了一部分养猪户。
村民大量搬入集市后,村子正在空心化。村里的老屋主要变成了存放稻谷粮食的仓库。每天,这些新搬入集市的村民们,都要走上几里路回家牵着耕牛去喂水,然后再给耕牛放点干草。随着机械化的普及,耕牛也在逐步被“解放”。
一些有钱人则到县城高安去买房子了。这个县级市的房屋均价已经到了四千多元,是北京10年前的房价水平。
那些从村里走出去的“能人们”,每年春节回家过年,都期待着下雪,而且最好是中到大雪。白雪,是这些“喝过墨水的人”最想给村子修饰的颜料。它能掩盖随处可见的牛粪、白酒瓶、泥巴、塑料袋,以及断壁残垣的祠堂,还有小时候差点淹死他们,而如今荒草疯长的池塘。
【吾乡吾民】“全民放贷”原来就在身边
过去两年,徐州民间金融机构突增。比银行高出许多的利息裹挟了大部分普通人。然而2011年下半年七八个人跑路,丢下了数千名受害者,并引发全城民间挤兑潮,进而可能拖累这个市场上的好公司。
身边的“放贷人”
一直以为,高利贷,只是自己和同事们采访报道的一种经济现象,和我总还是隔着些距离。却不想,这次春节回家,发现在老家江苏徐州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、观念保守传统的中原城市,竟然也在2011年成了高利贷的“灾区”之一。
腊月二十九,去初中同学家拜年。同学的妈妈徐阿姨知道我在媒体做经济报道,急急地拉着我问:“你说,2012年国家的金融政策会宽松吗?企业贷款会更容易些吗?”我讶然。这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,徐阿姨夫妇皆已退休,怎么会如此关心宏观经济,还问出这么专业的问题。
“我妈拿了一堆钱出去放贷,有一家跑路了,还有一家现在到期了却抽不出钱来,说是要等贷款批下来。我姨我叔还有我姥爷,都有放贷。”同学在上海工作,普通白领,也是过年回家,才知道全家都变成了放贷人,还出了问题。
想起来的路上,看到公交站牌、烟酒小卖店甚至电线杆子上面,到处都是大大小小、花钱的不花钱的投资抵押担保公司的广告,还觉得有些奇怪。原来一年没回家,徐州竟然也全民放贷了?
“我同事的儿子、我们楼下的儿子,原来都没有工作,现在都开投资公司了。才做了一年,就开起了小车。”徐阿姨开始详细说起她们家这两年的放贷之路。
最初接触到高利贷,是两年多前,徐阿姨的一个同事推荐的。12%的年息,也就是放1万元,一年能拿到1200元。只比银行略高一些,还是同事的亲戚开的公司,倒也稳妥。做了一年,本息全收,相安无事。
待到2011年初,徐阿姨再琢磨这笔钱的投资去处时,徐州忽然间多了很多类似的公司。而且看一家,年息18%,再去一家,年息24%;准备下单的时候又听说,年息40%、60%的大有所在。身边亲友参与放贷的也多了起来,都是你介绍我,我带着你的。
徐阿姨几经纠结,先选了一家在徐州有实体工厂的,年息24%,不高不低,投了5万元。又继续跟自己的姐妹们考察其它利息更高的公司。“反正退休了没事做,我们整天看看这家的工厂,听听那家的讲座。而且,放贷就跟有瘾一样,亲戚朋友又都热情高涨的,谁都觉得不会有事。”
挤兑潮
跑路那家的5万元,就这么在2011年6月份投了去。
老板是个徐州籍的日本华侨,号称投资了下属县级市邳州的一家热电厂,跟徐州老乡融资,有钱大家一起赚。60%的年化收益率,徐阿姨虽然觉得有些吓人,但看了很多跟政府相关的宣传资料,“政府总不会骗人吧。”
没想到才收了三个月的利息后,9月份就开始欠息了,老板跟放贷人们斡旋了两个月后,消失了。到区公安局去报案,徐阿姨才发现,已经登记了七八家高利贷老板跑路,几千号放贷人的信息。再细看那些登记信息,唬了一大跳,几十万上百万的不算少数,“就算是公安局把跑路的抓回来,怎么也会先还那些大头的钱,我们这5万10万的恐怕也指望不上”。
慌了神,徐阿姨决定,尽管看过实体工厂的那家应该不是骗子,但还是先抽出来落袋为安,反正12月底也到期了。
“抽钱的时候才知道,难啊。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,还得小声地到里屋去谈,怕影响了外面那些还在往里放钱的人,他们不高兴。”年前这几天,同学家几乎都在开家庭会议,讨论怎么把大家庭的钱,一笔笔地抽出来。
徐阿姨这一大家子,还有一堆钱放在了一家在徐州做了快十年的担保公司里。这家公司倒是只负责担保中介,合同由借贷双方直接签署。但2011年下半年徐州近十家涉嫌高利贷的老板跑路,也引发了这家公司的挤兑潮。
年前,这家公司连番邀请放贷客户开会,徐阿姨去了两次。“那老板很难过地说,我们马上都能开十周年庆功会了,什么风浪都经过了,没想到会碰到这次的挤兑潮。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们有实力,还奖励了不抢着提钱的人。”
“我知道他们也有难处。那家有厂子的公司,一直跟我说能不能续2个月,3月份生产销售能上来,贷款也有可能下来,到时候就能把本息都还给我们了。可是你说,这贷款能下来么?经济形势能好起来么?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么?”徐阿姨怕报道出来会引发挤兑潮,一直也没松口说那家厂子的具体信息,只是一直念叨着经济形势金融政策。
【吾乡吾民】垃圾包围农村
农民越来越富,污染却越来越重。毒垃圾渗入土地河流,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,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、吃的菜,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。

往日的盈盈碧水,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。 (陈新焱/图)
这次过年回老家,感受最强烈的现象之一,是垃圾污染。
老家地处大别山深处,取名“理畈村”。家的四周,是郁郁葱葱的大山,门前则是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。据说,清初就有人定居于此。从大山深处流来的泉水清澈见底,我的童年,基本上是在摸鱼捉虾、游泳戏水中度过。
那时,村民们也不打井。每天一大早,各家的男人们挑着水桶,就在河中取水。晨雾一过,妇女们就提着衣服,在河边洗晒。
大概在七八年前,喜欢打鱼的邻居抱怨,河里的鱼开始越来越少了;过了两年,乡亲们就不再在河里取水,转而挖井;再过了两年,井水也没人吃了,村里架起了水管,直接从小河的源头取水。
这样的变化,皆源于污染。而这种污染,几乎与村里的经济发展同步。
碧水良田成垃圾场
在大革命时期,老家是鄂东南苏区后方所在地,交通闭塞,贫穷落后,差不多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——乡亲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大米和蔬菜,吃剩下的,喂猪;人畜粪便则是天然的有机肥,生态平衡,几乎没有什么破坏。
直到我出生后的1985年,村里才修通了第一条通往乡政府的土路。几年之后,村里通上了电。工业文明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。
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有人外出务工,以后逐年增多,他们一部分在北京、西安做理石生意(因老家盛产理石);一部分在广东、浙江等沿海地区打工,至2009年,全村在外务工人数高达千余人。
外出的人们带回了财富,也带回了新的文明。这其中,变化最大的是,最近五年,几乎每家每户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二、三层洋房。
在泥砖瓦屋时代,为了方便积肥,村民的厕所基本和猪舍连在一起。换成洋房后,厕所移到了室内,增加了排污排水管道。难题由此出现——由于村里并没有统一规划,各家的污水便到处乱排。有的排到附近的田里,有的则直接排到了河中。
原来用的泥砖,拆掉之后打碎,又变成了泥土,在原来的地基上稍做平整,又是一块耕地。而现在换成了钢筋水泥,敲不烂,打不碎,村里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建筑垃圾。
富起来的乡亲们也开始消费工业品,化肥、农药、吃完就扔的罐头、各种包装精美的食品以及橡胶、电池、玻璃等各种化工产品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村庄。一些原有的优良传统,也在递增的财富面前瓦解。比如,原来谁家有红白喜事要办酒席,用的都是族人从家中带来的、自己吃饭的碗筷。现在主家都不麻烦别人,直接就买了一次性的塑料碗筷,吃完就扔。
问题随之而来。城市垃圾起码会有转运处理,而农村垃圾却无人顾及。乡亲们有的倒在屋角,有的倒在田埂上,有的则干脆倒入门前的小河里。
小河由清转黑,往日的盈盈碧水,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。而肥沃的耕田,有的也泛起了阵阵恶臭。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父母也忍不住哀叹:好好的一个村,就这么毁了。
垃圾场的城乡之战
这样的景象,并非只在老家出现。周边村也是如此。春节前,我在大理洱海边,一个名叫“文笔”的渔村采访,看到的情形甚至比老家还严重。这里的人们家里都没有厕所,村里建了几个公共卫生间——那真是我见过最臭、最难以插脚的卫生间——门口是苍蝇横飞的小山一样的垃圾堆,里面则是没有入池的一堆堆排泄物。污水从各家排出,在村中的小路中粘结成一团团黑色的胶状物。这些未经处理的垃圾,有的甚至直接入了洱海。
众所周知的是,在城市,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,2007年,上海市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。三年前,把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,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。而今当然更甚。
在农村,这一速度同样惊人,卫生部调查显示,目前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.86公斤,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,而这还不算那些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垃圾——统计数据显示,至少85%的城市垃圾,也被掩埋在了乡村。
在我老家就是如此。离我们村几十公里外,有一个名为凉亭岭的垃圾场,是老家所在县城唯一的垃圾场,使用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,如今的垃圾场内已形成一座十多米高的垃圾山,仅“山顶”的面积就有一个足球场大小。
2010年8月,附近的村民怀疑垃圾场污染了环境,导致该村癌症患者人数增加(该村约2600人,从1994年至今,共有37名村民死于癌症),堵封垃圾场二十余天。导致县城每日上百吨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,县城差点成为“臭城”(在其他地方,由此导致的冲突同样屡见不鲜)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过去农村垃圾主要是一些易腐烂的菜叶瓜皮,现在却成了塑料袋、废电池、农膜、农药瓶、工业废品、腐败植物等的混合体,特别是由于大量使用塑料,导致垃圾中不可降解物所占比例迅速增加,使得农村垃圾在日渐向“毒害化”发展。如果不加以遏制,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——那些有毒垃圾一点一滴渗入土地,渗入溪流,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,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、吃的菜,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。